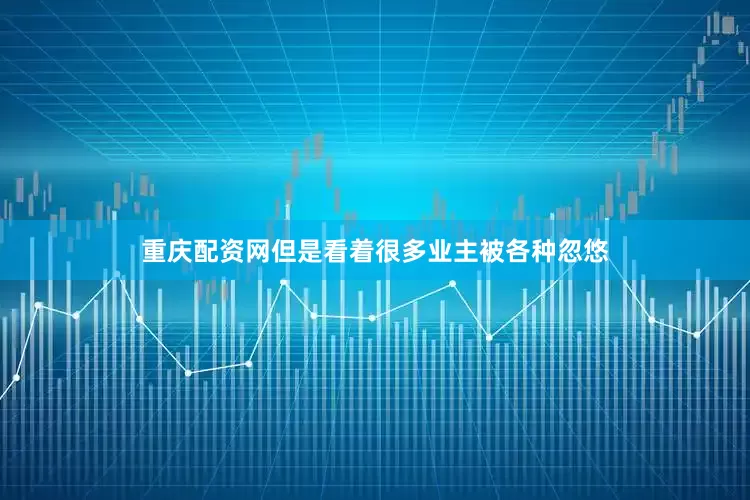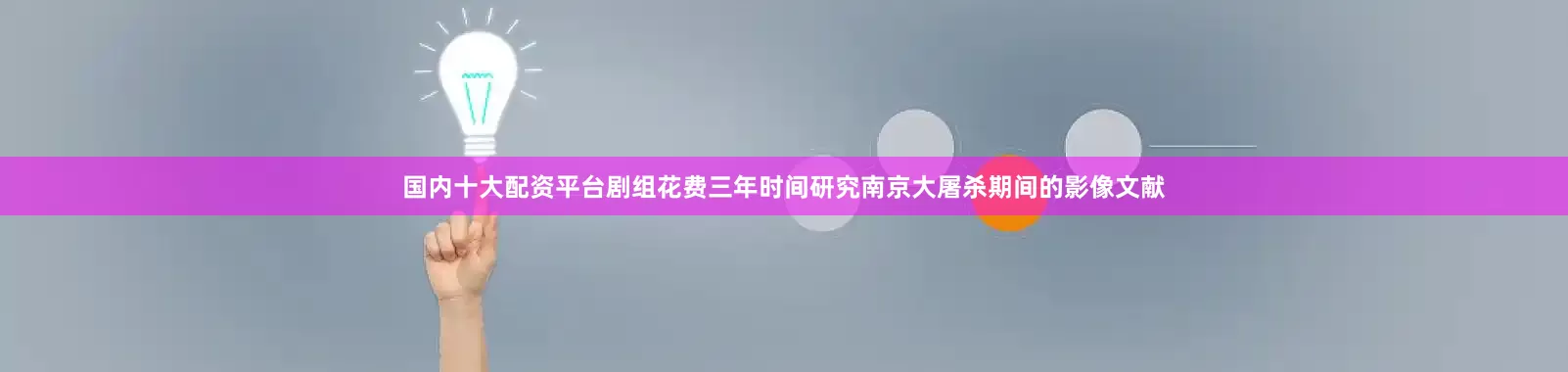

插图 | 鉴片工场 ©《南京照相馆》电影海报
作者 | 张力卜
在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后的88年,青年导演申奥以一部《南京照相馆》为这段沉重历史开辟了新的叙事维度。这部聚焦1937年南京沦陷期普通市民命运的战争剧情片,通过“吉祥照相馆”这一微观空间,将镜头对准一群原本只求苟活的平民如何在日军暴行面前完成从“求生”到“觉醒”的蜕变。影片以日军“亲善照”的拍摄与罪证底片的偷藏为主线,在显影液的化学作用与人性的道德挣扎中,完成了一次对历史真相的影像重构。
#电影南京照相馆#该片创作基底建立在严谨的史料考证之上。导演申奥在访谈中强调,剧组花费三年时间研究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影像文献,特别是《不许可写真集》中日军私自拍摄的暴行照片,以及约翰·马吉等国际人士的影像记录。这种对历史真实的执着追求,使得影片在虚构叙事中始终保持着与史实的紧密对话。其独特的“小切口”叙事,下文笔者将从剧情真实性的历史锚定、观点冲突性的人性博弈、观众普遍性的情感共鸣三个维度,结合导演创作手法与演员表现,系统剖析。

“亲善照”的历史骗局与影像反击
《南京照相馆》最具独创性的叙事支点,在于揭露日军“亲善宣传”的虚伪本质。历史记载显示,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日军为掩盖屠城真相,专门组织摄影队拍摄“日军与南京市民友好相处”的虚假影像,包括施舍粮食、分发玩具、医疗救助等场景。这些照片被制作成宣传册在国际上散布,企图扭转舆论对其战争罪行的谴责。影片通过毓秀等平民被迫参与摆拍的情节,将这一历史细节具象化。镜头前,她强颜欢笑接过日军士兵递来的糖果;镜头外,刺刀正抵在她家人的后心。这种“台前温情脉脉,台后血腥暴力”的强烈反差,在预告片里通过交叉剪辑形成震撼效果,左侧是“亲善照”拍摄现场的虚假笑容,右侧是同步发生的街头枪杀。
更具历史张力的是影片对“影像反击”的艺术再现。1938年1月,南京华东照相馆学徒罗瑾曾真实经历类似剧情,当日军少尉送来两卷记录屠杀场景的120“樱花”胶卷时,他冒险多洗16张照片,藏于毗卢寺附近厕所的墙缝中。这一“用胶片当武器”的平民抵抗行为,被编剧许渌洋转化为阿昌的“双重曝光”技巧,在日军要求冲洗的“亲善照”底片上,二次曝光暴行画面,使罪证在显影过程中自然浮现。这种处理既保留了历史原型的核心精神,又通过电影语言强化了戏剧冲突,正如导演申奥所言:“我们要让观众看见,每个暗房都是战场,每台相机都是武器。”

文化侵略的视觉叙事
影片超越了传统战争片对军事暴行的聚焦,首次将镜头对准日军的“文化掠夺”策略。历史学者孙宅巍在《南京大屠杀研究》中指出,日军在南京实施的是“物质-文化”双重灭绝政策,仅1938年1月就有超过3000箱文物被制式化打包运回日本。《南京照相馆》通过三组平行蒙太奇镜头呈现这一维度:日军军官小心翼翼擦拭宋代瓷器的特写,与平民被随意枪杀的全景交叉剪辑;古籍被分类装箱的工整画面,对比城墙被炸塌的废墟场景;“东亚共荣”的宣传标语,覆盖在被焚毁的夫子庙牌匾之上。这种视觉对位不仅揭露了侵略者“文明外衣”下的野蛮本质,更暗示了文化灭绝比肉体屠杀更阴险的危害性。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对历史细节的考证精确到道具层面。照相馆内悬挂的《良友》画报、墙上的月份牌女郎、老金(王骁饰)使用的德国产“蔡司”相机,均符合1930年代南京中等商户的典型配置。这种对物质文化史的尊重,使得虚构剧情获得了坚实的历史质感。申奥与编剧团队并未将角色塑造为非黑即白的道德符号,而是通过七个平民在照相馆内的封闭空间中,展现了人性在生存压力下的复杂光谱。这种对“灰色地带”的直面,构成了影片最具思想锋芒的部分。

刘昊然,从“精致利己”到“觉醒平民”的表演蜕变
刘昊然饰演的邮差阿昌,打破了他以往在《唐人街探案》系列中的“少年天才”银幕形象,塑造了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普通人”样本。角色初期的“精致利己主义”通过身体语言精确传递,躲进照相馆时环抱膝盖的防御姿态,偷藏干粮时眼珠的快速转动,面对日军时下意识的谄媚微笑。这些细节构建了一个在乱世中只求保全自身的小人物画像,与传统战争片中的英雄叙事形成鲜明对比。
角色的转变发生在暗房显影的关键场景。当阿昌首次看到同胞被砍头的底片时,刘昊然通过“瞳孔震颤-呼吸停滞-手指蜷缩”的生理反应链,展现了良知对本能恐惧的压制。特别是他在显影液中颤抖的双手,既想扔掉底片保命,又无法直视暴行的矛盾心理。这种转变并非突然的道德升华,而是通过三次冲洗底片的递进式设计完成:第一次被动参与,第二次犹豫偷藏,第三次主动冒险,最终在排水管前用身体护住罪证的牺牲,实现了从“小我”到“大我”的艰难跨越。

高叶,职业梦想与历史创伤的破碎与重生
高叶饰演的龙套演员毓秀,代表了战争中被摧毁的“平凡梦想”。这个总对着小镜子练习微笑的年轻女性,将“成为胡蝶那样的电影明星”作为人生目标,却在日军的枪口下被迫扮演“亲善照”中的道具人。高叶通过声音控制与微表情的精细处理,构建了角色的三重心理维度,谈及梦想时声线的轻盈上扬与瞳孔的明亮光芒;面对日军时面部肌肉的僵硬抽搐;目睹屠杀后声带振动的颗粒感变化。特别是她与王传君的对手戏中,当翻译王广海劝她“别惹事”时,高叶用“直视对方颤抖的双手-缓慢摇头-嘴角牵动”的沉默表演,传递出“清醒的绝望”,这种“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始终不落下”的克制,比嚎啕大哭更具情感穿透力。
毓秀随身携带的褶皱戏服成为重要的象征道具。高叶设计了“抚摸布料时的温柔搓捻”与“遇险时的死死攥紧”两种道具互动方式,前者代表对艺术梦想的执念,后者则转化为保护罪证的决心。当她最终用戏服包裹底片传递出去时,这件充满个人梦想的物品便升华为承载民族记忆的容器,完成了从“小我梦想”到“集体记忆”的意义超越。

王传君,“合作者困境”中的道德摇摆
王传君塑造的翻译官王广海,是影片中最具伦理争议的角色。这个精通日语的知识分子,为换取生存特权而为日军服务,却又在暗中给照相馆送药、传递消息。王传君通过“分裂式”表演呈现这种矛盾,对日军军官时弓腰谄笑、日语发音的刻意谄媚,独处时用烧酒猛灌自己的痛苦,以及目睹同胞被带走时眼球的快速躲闪。这种“半睡半醒”的生存状态,精准捕捉了历史学家所称的“合作者困境”。在极端环境下,道德选择往往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在“害人和害己”之间的残酷权衡。
角色的高潮戏出现在日军搜查处决前夜。当王广海将通行证塞给阿昌时,王传君用“台词中断-喉结滚动-不敢直视”的表演细节,展现了背叛身份的内心挣扎。这种处理避免了对“汉奸”角色的简单化批判,而是引导观众思考,在生存与良知的天平上,普通人究竟能承受多大的道德压力?正如申奥所言:“王广海不是反派,他是战争绞肉机里的另一种受害者。”

“沉浸式创伤”的美学建构
与《金陵十三钗》的宏大战争场面不同,《南京照相馆》90%的场景集中在100平米的照相馆内。摄影指导曹郁采用“暗房红光”作为视觉主调,当显影液流过底片,暴行画面在红色光晕中逐渐浮现,这种“限制性视角”比全景式展现更具心理冲击力。当阿昌颤抖着举起底片,银幕上的血渍仿佛滴到了我脸上。这种“近距离创伤”打破了历史与当下的时空隔阂,使1937年的苦难获得了情感上的即时性。
影片对声音设计的匠心处理同样增强了沉浸感。音效师富康采用“三层声场”架构,表层是日军皮靴声、相机快门声等环境音;中层为角色压抑的呼吸与心跳;深层则是若隐若现的秦淮河画舫音乐,暗示被摧毁的和平生活。这种声音层次在“亲善照”拍摄场景中形成强烈反差,摄影机快门的机械声与背景里的零星枪声重叠,虚伪的欢笑声下是角色紧张的心跳声,让年轻观众在感官层面直观体会“平静表象下的恐怖。”

演员“破圈“效应与历史教育的影像实践
影片的市场号召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主演阵容的“破圈”表演,刘昊然的“少年感撕碎”、高叶的“大嫂反差萌”、王传君的“演技神经质”等等。当看到电影里日军打包文物的场景,突然想起博物馆里那尊'昭和十二年十二月 南京'字样的陶罐,原来历史书上的'文化掠夺'四个字,背后是这样具体的罪恶。这种将银幕叙事与实物史料结合的教育方式,使抽象的历史概念获得了情感温度。
影片中“普通人保存罪证”的情节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否认历史的声音仍存的今天,《南京照相馆》告诉年轻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历史的守护者。”据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已计划将影片相关片段纳入常设展览,作为“当代人如何记忆南京大屠杀”的鲜活案例。
线上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